编者按:本周推送孙惟以伦的《“画屏”背后空间叙事的重新思考》(原载王璜生主编、沈森执行主编主编《新美术馆学》研究文辑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作者通过对苏州博物馆2019年9月举办的展览《画屏:传统与未来》的考察,运用“对话”理论来论述展览实践中的“空间叙事”问题,试图阐述“空间叙事”的三个“对话”板块,即“文本-意图”、“展览-空间”和“叙述-体验”。文章以博物馆展览为切入视角,论述了三者构成展览的“互文性”对话,也初步探讨其对于美术馆的借鉴可能。
引言
在学界多元的研究触角不断展开的同时,博物馆从业人员也正不断地开展带有“实验”精神的展览实践。苏州博物馆(后文简称“苏博”)在临时展览的实践俨然成为了一种博物馆行业另辟蹊径的做法,即一所地方博物馆致力于打造艺术展。“苏博”新馆自建馆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博物馆空间内打造现当代艺术展,并获得了广泛好评。近十年内,通过机构自身学术能力的增强补足,馆内的艺术展从原先单一地邀请著名艺术家举办特展的形式,逐渐开始建立立足自身馆藏,具有学术体系的学术系列展,例如自2012年起举办的《吴门四家》系列展和始自2016年的清代藏家系列学术展。不同于通常博物馆和苏博自身以往的做法,具有延续性的学术系列展使得苏博不仅在业界获得良好的口碑,也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好评。

图1:苏州博物馆
然而在我国公共文化教育之语境下,美术馆与博物馆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场域:前者以审美为导向,着重于感官(视觉)体验;后者以时间为线索,使得叙事成为了题中应有之意,乃至一种“必须”的存在。审美与叙事,这种明晰的功能划定的边界使得美术馆与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教育中有了明确的分工,继而以各自的体制和机制进行独立的展览实践,但同时朝向各自“功能本色”的方向追求“极致”,却又更多地带来了某种自缚式的掣肘。比如美术馆在叙事上走向弱化,而博物馆忽视了审美上的体验。因此有人追问美术馆的叙事性,比如曾玉兰在论述当前美术馆所举办的艺术展时指出西方艺术史上的著名艺术家展览,西方当代领域里已成名的大牌艺术家展览和强调视觉快感的网红消费展虽然做到了部分艺术普及的工作,但实际上与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无甚关联[1],因而与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美育”之目的相去甚远,故抛出了“美术馆是‘视觉游乐场’吗?”之问。言下之意,当美术馆作为有形空间的同时,如何通过在物理空间的展览实践使得这种有形空间与观展者的精神空间紧密结合成为了当下美术馆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2:苏州博物馆
反观博物馆业界,自新博物馆学从上世纪90年代盛行以来,博物馆学的研究视角开始逐渐转向其社会功能,即彼得·维尔戈所说的“彻底重新审视博物馆在社会中的角色”[2]。国内外学者在新博物馆学的助力下都在不断追问一个问题:博物馆究竟是“神庙”还是“论坛”[3]。而关于“神庙”与“论坛”在我国博物馆行业的争论更因为其特殊的语境而显得有趣。一方面,在官方权力背书的情境下,博物馆展览内容拥有了“不言自明和不可挑战的神圣性”[4],使得其教育职能被固化为单向的知识输出;另一方面,博物馆作为非正规教育机构,又在试图探寻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具体为关注社会文化消费需求、博物馆的社会关联与社会责任等等。正是这种对于新型关系的探索,使得博物馆内的具体工作发生了从“物”到“人”,从“单向”到“互动”的转变。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和质问展览的叙事功能,及其如何优化和创新的问题。因此,本文将通过剖析苏博的艺术展览实践,继而论述博物馆如何转译“神庙”与“论坛”的关系及其对于美术馆的借鉴可能。
一、从苏博《画屏:传统与未来》看审美与叙事
2019年9月6日,名为“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后文简称为“画屏”展)于苏博开幕。此次展览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美术史学教授巫鸿先生担任策展人,而展览也是基于其 1996 年有关屏风的研究著作《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展开的。在《重屏》一书中,巫鸿教授将屏风作为一种媒材理解与回答“什么是传统中国绘画”。相较于研究著作,他在展览伊始举行的公众讲座中阐释到此次展览的意图是在博物馆中通过与屏风相关的展品进行一场“古今对话”[5]。而“古今对话”意在通过展览展示昨天艺术史中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母题(motif)在今天乃至明天的延续。这与苏博近十年学术系列展的思路中的延续性是不谋而合的。至此,策展人本人即学术专家的身份无疑使得“画屏”展的学术基础得以大大提升;汇集国内外14家知名博物馆的馆藏展品与9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展览也让苏博通过前期宣传紧紧抓住了公众的眼球。清晰的展览主题,扎实的学术支撑,精彩纷呈的展品与清新脱俗的形式设计,种种迹象都表明苏博本次的“画屏”展理应为一场叫座又叫好的文化盛宴。

图3:“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海报
出人意料的是,本次展览的结果却是差强人意,不论在馆内还是业界都遭遇到毁誉参半的境地。在众多评论中,名为《银烛秋光冷“画屏”》的一篇展评脱颖而出,文中这样写道:“苏博‘画屏: 传统与未来’展最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他们将屏风作为整场展览构成与叙事中最关键、而且是唯一的元素,除了这些‘屏风展品’之外,整场展览的构成与推进缺少必要的叙述与逻辑[6]”。需承认的是,在新博物馆学带有强烈批判性的视角下,这篇展评相当中肯地点出了苏博,乃至是中国博物馆行业的些许通病。但是,回到本文最开始的立脚点,即美术馆与博物馆对于审美与叙事所不同的侧重,对于艺术类展览实践(不论在任何机构的展示空间内)过分苛求叙事是否理所应当?换言之,假设“画屏”展不是由苏州博物馆承办,而是苏州美术馆,观众是否会对于叙事有如此高的期待?

图4:“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现场
理应澄清的是,本文不是单就上述展评的反驳,更绝非为苏博正名,而是希望通过对于“画屏”展的案例及前文展评中提及的关于“叙事”问题,分析苏博对于空间叙事的探索。本文将以笔者在苏博所进行的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资料为数据,所采用实证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参与式观察以及针对苏博策展团队成员所进行的半结构采访,在同时是“参与者”与“旁观者”身份的前提下,秉持田野调查的原则,尽力保持客观严谨的态度,旨在从苏博主办的“画屏”展览实践中的“空间叙事”以探求叙事之于美术馆展览空间内意义建构的些许启示。
本文之所以选择苏博的“画屏”展作为个案来进行理论分析,正是它作为博物馆展览兼具美术馆展览的某些特性。理论的分析功能是为了批判和建构。不论新博物馆学作为一场学术运动也好,或是一种学术精神也罢,尽管其作用在博物馆内虽不是立竿见影,但却能够使思考与实践相辅相成。同样美术馆理论的反思创新与美术馆实践之间必然也存在这样的张力。博物馆理论与美术馆理论在更高层级上是具有某些相通性的,因此我们借助空间叙事的“对话”理论,可以打通对两者的观察渠道。
二、“空间叙事”的定义
不论是美术馆抑或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其根本的原则是关于信息的传播。对于美术馆而言,“美”本身即是一种信息。借由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所创造的概念“Carnal Ec-ho”——描述画家如何将可见世界内化到他们的身体图式中,然后创作出既能表达可见世界又能表达其个体体现状态的作品 [7]。因此,当观众在徜徉在美术馆内欣赏艺术作品时,美作为唯一的信息将观众带入了这种既有客观世界,又有艺术家情感存在的精神空间之中。因此,审美就是谈论“美”是什么。而就博物馆来说,知识即信息。权且不论它是“神庙”或“论坛”,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中的知识必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只是不同博物馆如何传播这种知识罢了。在博物馆学日益发展的浪潮中,知识的传播从知识点开始,由点到面,现在更多的学术讨论着手于如何从面发展到体系。在这种认识的层面上,叙事显然是一种最聪明的,最吸引人的知识传播手段。
所谓叙事,必然包括作者,故事,叙述行为与读者四要素,其中每一个定义在学界都或多或少经历了非议与挑战,例如罗兰巴特所提出的“作者已死”的论调。为行文便宜,笔者在此处引用了英国博物馆学者翠西亚·奥斯丁的对于这四要素的定义。在她看来:“作者,赋予了意向性的概念;之于故事,需具备戏剧冲突与所应展开的故事内容;在讲述方面,应具备多感官交流的概念;针对受众,提出了个体与群体接受、体验和意义建构的概念”[8]。在明确了叙事及其四要素的基础上,仍需进一步认识何为“空间叙事”。
为了使传播变得更为有效,叙事既是制定空间序列的装置,又是服务于构建有意义的参观体验的认知工具[9]。观众参观的行为其实质是有感知力的个体在有形空间中(博物馆或美术馆建筑),基于其之前的经验(阅历与知识的积累),对于展览中各种符号的解读。之所以要特意强调有形空间是因为空间体验给予观众由展品组合构成的形象系统[10],而它则拥有整体表达的能力。这也是观展与读书、看电影等其他形式传播的最大不同。这种不同使得博物馆与美术馆内的叙事与文字、图像、影音等媒介内的叙事大相径庭,故而称之为空间叙事(Spatial Narrative)。空间叙事的具体体现就是借助馆舍的空间帮助叙事更有效地传达。如若将奥斯丁的四要素模块化置于展览实践的流程中,就是:意图—文本、展览—空间、叙述—体验(观众体验)。意图—文本显然是该流程的第一步,即展览策划。展览—空间,是在展览实践的第二步,即通过空间设计展览方式。叙述—体验是展览实践的第三步,是指在借助空间完成叙述行为,尽力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这是本文想要重点阐述的三个围绕“对话”而形成的板块。

图5:“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现场
三、文本——意图
展览前期策划是“意图”制造产生的阶段,其中主要分为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两部分。这两个部分均是由“作者”设计以突出展览的“意图”的,显然也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实践的。首先,须厘清的是展览的主题与展览的意图绝不能划等号。前者是展览内容的核心,内容设计必须围绕它来进行策划;后者更接近于传播目的,是“贯穿于展览建设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和表现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于展览策划设计和表现的全过程”[11]。因此,意图应当是建立在主题之上的。
在巫鸿确定“画屏”展的主题为通过画屏的“传统与未来”之后,有两个不争的事实:其一,“画屏”展的内容将完全不同于策展人巫鸿的著作。《重屏》一书只能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支撑材料,而绝非展览内容的“施工图”。其二,“画屏”展是展览,但不是纯粹审美的画展,也不是纯粹叙事的文博古董陈列展。其三,巫鸿先生因为身在美国,很多具体事务需要苏博的策展团队进行实施,这使得展览的内容深化与具体落地都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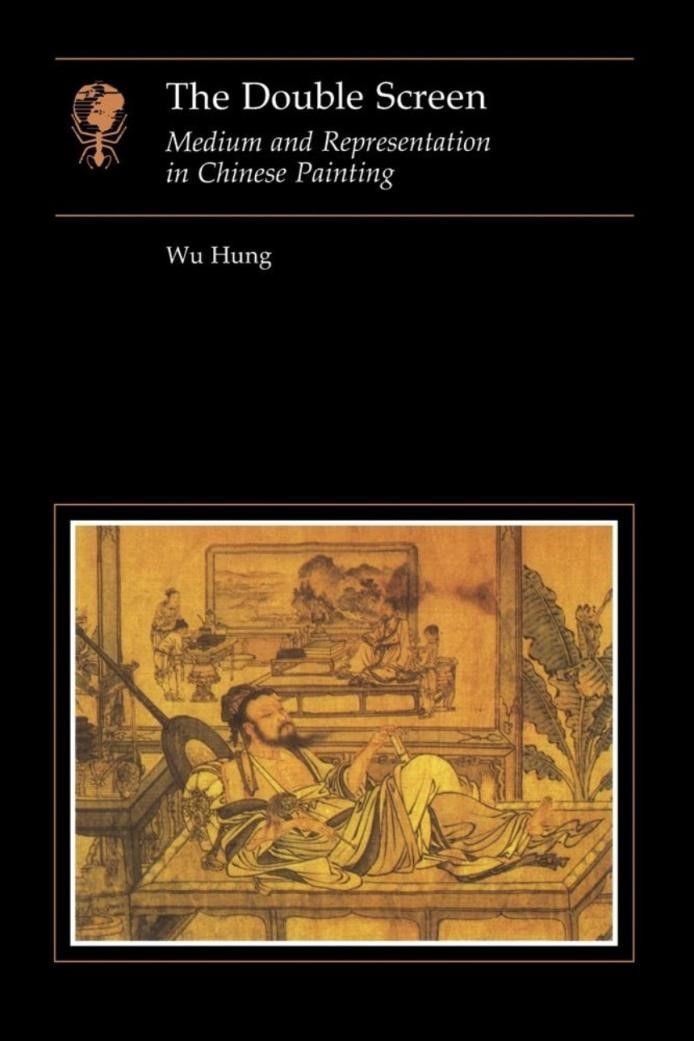
图6:巫鸿《重屏》英文版封面
“传统与未来”这是一个较为笼统庞大的主题,巫鸿实际上的意图是要完成一种古今“对话”。那么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今对话如何可能?
这种“对话”从理论上考证,是有依据的,这就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词是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向西方世界介绍前苏联米哈伊尔·巴赫金(M.M.Bakh- tin)理论时创造的。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是当今文学批评和话语分析中使用最广而又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由于它突显了现代文化生活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性,因此是个十分有用的术语 [12]。巴赫金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关注语言活动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更关心语言(包括我们的展览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各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而始终将它们纳入历史和社会的范畴。
我们如果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加以认真理解的话,就知道:所有话语都是对先前话语的回应, 我们在特定情景中所选择的话语都包含着“他者性”(otherness),即它们属于特定的语类,带有先前话语的痕迹:“用于表达个体意识的语言存在于本人和他人之间的边界线上。[13] 语言中的词语一半是他人的”[14]。词语是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才成为言者自己的词语,这意味着词语永远不是独自存在的,而总是已经饱含着他人的词语和他人使用的痕迹。正是语言的这种“他者性”,为巴赫金理论中的“对话性”(dialogism)概念提供了解释[15]。

图7:徐冰《背后的故事:仿大痴山水图》在“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现场
把展览的“文本—意图”纳入巴赫金以及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 那么意图之下的展览主题与文本,甚至其他方面,都具有“互文性”之特点。策展人——无论美术馆还是博物馆,在设计文本阶段就是 利用这种“他者性”资源把意义“挪用”到自己的意图之中。画屏、瓷器、油画或者某一只篮球,这些物件本身具有“他者”以往的体验和认知,即便儿童观众对一只皮球也有体验和认知;策展人要“挪用”这些已有的体验和认知。因此,策展文本内容的细化和深化,就不能只是“我”的立场,而同时要有“他者性”立场,这包括展览前的“他者”和展览中作为观众的“他者”。这就是关注了“主体间性”——主体之间的对话与潜对话正要凭依于这种“间性”的存在。换言之,把古代传统和现代受众均纳入意图的设计之中,也把当代人的认知纳入文本的范围来建构意图。
从巫鸿策划的“画屏”主题“传统与未来”这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主题下的“古今对话”,当然地包括“我”与“他者”的对话。他不是简单地把画屏不作选择、不作排列地机械堆积到展厅里。从古代到当代中国人生活中,画屏具有“三位一体”的独特身份:它既是一种绘画媒材,又是生活中可供近距离欣赏的生活物品,还是建构室内外空间的辅助性建筑构件。这一特性使屏风在古今生活和传统美术中,扮演了耐人寻味的角色。巫鸿指导苏博的策展团队,把展厅设计为“屏与礼仪空间”、“物的画屏”以及 “屏风入画”三个展览部分;把空间、物品和图像这三个基本元素融入这场综合性展览,进行了艺术的再度创造。这时的“画屏”展,既不是单纯依赖其学术著作,也不是策展人个人意志的体现;此处的“我”已经是巫鸿、苏博策展团队、各种画屏及古代书画、器物、墓室壁画以及当代艺术创作等多个方面所构成的“我”。这里,“我”与“他者”的“互文性”对话已然存在于其中,是围绕着“我”和“他者”的叙事。这里不仅有主题,其背后还有“意图”,而且不是“我”一人之意图,还是“我”与“他者”进行“对话”后的意图。这就是“文本—意图”中间融入了“互文性”对话的策展实践。

图8:展望《山水镜》和《不锈钢木家具》与施慧《本草纲目·2》在“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现场
当然,这个案例本身就是“传统与现代”主题下的对话,它过于典型,反而淡化了这种“互文性”对话的内在机制。好在,“互文性”对话在“展览—空间”环节仍然存在而且不可或缺。在有了“文本—意图”内容的框架之后,策划团队的下一步展览实践工作是如何进行空间形式设计让展览落地,并且能够一以贯之地将展览意图融入展示空间内。
四、展览——空间
作为2019年度临时展览的重中之重,“画屏”展所使用的展示面积是苏博所有临展中史无前例的。除了保持常设陈列,苏博使用了几乎所有可用的展示空间为“画屏”做嫁衣。因此,当分析这个展览与空间的关系之前,必须要对苏博的建筑空间有所了解。
被誉为最后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贝聿铭先生借鉴了拙政园内中国古典的“叠山理水”的理念,并将之融入了苏博新馆内。他在设计前参观苏博库房时被一副元代临米芾的山水画中的意境所打动,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16]。因此,新馆建筑虽以钢筋混凝土为材,但其墙面却如园林内置建筑般进行粉饰;主体建筑虽然在结构上模仿了中国古代房屋的木式结构,但却在室内融入了他炉火纯青的玻璃构造,将自然光引入展厅内部。白墙加自然光的感受使得观众在室内观展如同在街市信步,给人以自然平和的亲近感,消除了传统博物馆中黑暗压抑的压迫感。贝老将苏州传统的粉墙黛瓦融入到现代建筑中,结合自身优势所演化出的创新充分地体现了“中而新,苏而新”的特质,使苏博新馆成为了苏州名园的现代化延续。

图9:苏州博物馆内景
贝老在耄耋之年接受家乡的邀请,使得他对这座被称之为“自己的小女儿”的博物馆格外钟情。在对苏博新馆进行建筑设计之前,他对博物馆室内空间有了充分的构想。自明代以来,苏州在中国艺术界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书画造诣最深的四位艺术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瑛皆是苏州人,因而使得“明四家”又称之为“吴门四家”。这四位艺术家在中国家喻户晓,因而使得他们的书画成为了苏博馆藏的精品。此外,苏博自建馆以来一直致力于征集、收藏吴派书画以及吴派源流诸子的作品,这使得馆藏书画以明四家为基础,又容纳了清代苏州的四王以及后期民国大家的书画作品。基于对馆藏藏品的了解,贝老首倡在苏博新馆内设置现当代艺术厅,因为他想让苏州的文脉在这座博物馆内得以延续。也正是这种先见之明使得若干年后一场关于“传统与未来”的展览得以成行。
尽管观众在苏博新馆内的参观是自由随性的,但策展团队还是制定了一条展线——的确也是最为理想的展线,应当是从东廊负一楼临展厅到二楼书画厅,最后返回一层由东廊至西廊,参观完现当代艺术厅,最后从忠王府出馆。这条展线的设计是基于本次展览“古今对话”主题及其内容设计的。严格意义上,博物馆展览内容是由展览意图决定的,因为文物的甄选与前期内容深化有着必然的紧密关联,且借调工作已然完成。本文之所以将内容(文物)放在空间部分,是因为在探讨叙事的大前提下,“故事”本身与“叙述”即如何讲故事是密不可分的。
“画屏”的古代部分围绕着传统意义上画屏的功能进行展开,分别为“屏与礼仪空间”、“物的画屏”与“屏风入画”共三个单元。前两个单元设置于负一楼临展厅的,展品的时间跨度从战国时期直至清朝晚期。而第三单元“屏风入画”顾名思义是由书画藏品组成,时间跨度从五代至民国时期,因而被置于二楼的书画厅。在负一楼临展厅当中,观众从入口处就可以看到象征皇权的龙椅与屏风;之后的《东魏武定元年翟门生屏风石床》更是现今发现最早的带有屏风的棺椁,以显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沿展线来到第二单元,多数清代的屏风器物都能够让观众立马与脑海中的屏风进行联系。哪怕是作为文玩置于书桌案台的插屏,也保持着传统意义上屏风的造型,只是尺寸大大缩小。但是细看前两个单元,会发现之间的衔接处出现了一组“突兀”的藏品——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墓地的七副绢本唐彩绘。

图10:清乾隆剔红围屏、宝座与东魏武定元年翟门生屏风石床在“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现场
之所以“突兀”的原因在于其所处展示空间。观众置身于“屏与礼仪空间”和“物的画屏”这两个单元应当能料想到他们所能看到的藏品或多或少与曾经了解到的屏风差不多。但是这七副绢本唐彩绘无论从外形还是其图像所包含的信息均与传统意义上的屏风无关,哪怕再怎么牵强附会,也应当放置在二楼的“屏风入画”单元。根据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苏博策展团队在考虑这七副绢本唐彩绘的空间位置时,主要是基于其年代进行考量的 [17]。尽管“画屏” 是一个艺术展,但在展示屏风传统性的展厅内,博物馆展览又迫使 “必需”的时间线索回归,成为推进叙事的逻辑。而二楼书画厅内的展品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作为艺术展的重头戏,书画部分的展品包含了许多本次展览的压轴展品,例如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重屏会棋图》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明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卷》。但是,不少作品中的“屏风”存在感不强,例如沈周的《岸波图卷》与张大千的《仕女拥衾图》。在偌大的展厅中,观众视力所及的符号有太多太多,有看人物的,有看服饰的,有看落款或提拔的,有看文字说明牌寻找基础信息的。当观众愈认真地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符号时,他们也在离展览的主题——屏风,愈来愈远。

图11:传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局部)
这两个位于不同楼层的例子都在说明“画屏”的“故事”,也就是甄选出的展品,似乎在不停地试探展览主题的边界,也在挑战观众对于他们心目中“屏风”的定义。因此,当空间引导整个“故事”推向高潮的时候,观众将在自己的思考中建构属于自己的参展意义。这就是空间对于展览叙事的意义,也是观众体验的开始。
五、叙述——体验
在文本中,故事平铺直叙显然会让读者索然无味,而精彩的故事往往都会有跌宕起伏。这浅显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博物馆内的叙事,只是促成高潮的手段不尽相同。这些促成高潮的手段即是利用空间来完成“叙述”这个行为本身。在“画屏”展中,“古今对话”的高潮显然是当“传统”与“未来”相遇时。就事论事,若观众依照设定的展线在苏博的建筑空间内浏览,三个临时展厅的空间布局显然相对独立,尤其是“传统”部分的三个单元被分别置于负一楼与二楼。同一部分的内容在有形空间内被割裂,使得整个叙述行为支离破碎。正如前文中展评的论点所指出的:“展览中几乎没有任何内容可以传递出文本的内在逻辑”[18]。这无疑是本次“画屏”展的硬伤,我把它看成是叙事空间上的硬伤。空间割裂的客观原因曝露出苏博策展团队在释展工作方面的不足,也解释了叙述不连贯的原因之所在。平心而论,作为一名观众,以展评作者的立场置身于“画屏”展中,这种不连贯的叙述让观众很难有良好的参观体验。即便精品文物自身所拥有的的价值足够表达丰富的信息,对于相对陌生的观众来说,说明牌上提供的信息还是太有限了。策展团队成员在事后谈论这个问题时也承认:“应当在重要节点上把握文字的度。重点文物,重点照顾。”[19]
但是,参观体验难道仅仅是源自有形空间带给人的生理感受吗?“画屏”展意图中所包含的“互文性”揭示了我和他者、展览与受众“间”的互动规律。“传统的故事”在不断试探屏风定义边界的同时,也在不断促使观众反思并挑战自己精神空间内已经固化的屏风定义。当他们抱有具备怀疑态度的思考从“传统”迈向“未来” 时,有形空间的割裂又在无形中为观众提供了沉思的暇余。带着 “屏风究竟是什么”的疑问,观众从展览的古代部分走向现当代部分,“古今对话”在有形空间内完成。而从“画屏”展现代部分好评如潮的反映来看,这种通过物质空间制造的经历在精神空间中引发的思索,在不经意间将这场“古今对话”推至高潮。屏风,曾经作为中国人所熟识的间隔室内外空间的辅助性建筑构件,在展览的尾声悄然变成了含括室内外空间的,而这得益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宋冬的作品《水屏》。

图12:宋东作品《水屏》 在“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现场
两扇用磨砂玻璃构成的巨大弧形的屏落在忠王府正中央,形成影壁屏。观众从两侧进入双弧屏组成的空间,用宋冬准备的毛笔与清水在磨砂玻璃上参与“画”屏的行动。背景中的忠王府作为苏博老馆的馆舍,象征着传统,而圆形弧屏坐落其中赋予古典建筑的传统空间以当代性;同时,忠王府作为苏博的出口,意味着所有观展活动的结束,通过在圆形弧屏内的互动,将引发的思考延续至展览结束后;更为重要的是,《水屏》作为古老屏风的当代延续,将屏风原有的间隔功能转化为含括功能。其坐落于苏博新馆的组成部分内,正象征着苏州博物馆走向更具包容性的明天。因此,策划团队将《水屏》安置在展览的尾声,其意义已经远超于那种简单的互动装置了。“画屏”展饱含“互文性”的意图将整个故事巧妙地在有形空间中进行了设置,使得每一位观众个体都以自身的体验建构了独立的意义。展览最后升华成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表征,又使得先前具有强烈个体性的意义建构在观者的精神空间能够引发共鸣。

图13:宋东作品《水屏》在“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现场
余论
如果单纯按时间线索来排列画屏陈列,试图叙述画屏故事,那它的叙事性就会很弱,空间要求也就不高,“互文性”对话可忽略不计,展览意图也就完全缺席——那么这就成为一次普通的、平庸的展览。相反,“画屏”展的创新就在于此。打破墨守成规的叙事 逻辑和习惯,它恰恰是按照文本—意图、展览—空间、叙述—体验这三对关系,来进行空间叙事和“互文性”对话的。由此,观众的体验得以成为以列斐伏尔式的空间生产中所产出的那种被称为“具体普遍性”(abstractions concretes)的产物,即特殊性(社会空间)—普遍性(逻辑数学意义上的精神空间)以及个别性(自然的或感知的现实“场所”)的统一[20]。硬伤是存在的,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在 空间叙事中应当灵活运用“空间”之重要性,妥善处理空间序列以 规避可能引发的不适。另一方面来看,至于观众的体验甚至褒贬,或者说展览中的“对话”的不一致性,它告诉我们,空间叙事对话 中的“复调性”或者展览符号的“重音性”、“多重音性”特点,就像音乐创作中多声部同步进行的“复调音乐”。艺术展览的“对话”,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都是围绕一个作品,所以构成对话的“复调性”。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符号中反映的存在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符号的折射。而这种折射是由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在同个符号集体内引发的争论[21],既包含在整体之中,又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本文以苏博的“画屏”展为例,从上文论述的文本—意图、展览—空间、叙述—体验三个“互文性”对话板块中不难看出,在空间叙事里,空间作为叙事的落脚点贯穿于整个展览实践的全部过程中。但是在不同的机构内,客观存在的空间各不相同,因而也决定了空间叙事的方式绝不是唯一的,而是纷繁多样的。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主张美术馆都朝向叙事性功能发展,而是探讨:在美术馆展览实践中是否要关注它同样存在的意图—文本、展览—空间、叙述—体验三个互文性对话板块。
与博物馆相似,传统美术馆“殿堂化”和“精英化”的策展思路是否需要反思?是否有必要从精英话语、经典话语向平民话语、现代话语作适度的转移?美术馆的审美主体应该是更广泛的审美人群而不再是仅限于专业人士。基于这个认识,美术馆应当如何增强其叙事性特别是空间叙事,以补充审美性功能是当前亟待斟酌的问题。美术馆在关注审美功能、服务于展览意图的前提下,如何增强空间叙事功能,特别是空间叙事中的“互文性”对话,从而达到观众体验的最佳状态,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细究的课题。
孙惟伦 | 英国莱斯大学博物馆专业博士
注释
[1] 曾玉兰.美术馆是“视觉游乐场”吗?[J].上海艺术评论,2019(6).
[2] P.Vergo.The New Museology[M].London:Reaktion Book,1989.
[3] D.Cameron,The Museum,A Temple or the Forum[J].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1971,14(1);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4]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3.
[5] 巫鸿:《古今对话——以画屏为例》讲座[EB/OL]. http://www.szmuseum.com/Activity/ActivityShowReview/687bd5c06cef-4ba1-8633-577386ed5ce4?type=0
[6]赵墨.银烛秋光冷“画屏”[J].中国美术报,2019(4).
[7] R. McCann. Entwining the body and the world: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experience in the light of “Eye and Mind”[J].in G. Weiss.Intertwinings:Interdisciplinary Encounters with Merleau-Pon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8] T.Austin.Scales of Narrativity[J].in S.MacLeod,L.H.Hanks and J.Hale(ed.) Museum Maing: Narratives,Architectures, Exhibi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2:116.
[9] 同105.
[10] 严建强.论博物馆的传播与学习[J].东南文化, 2009(6).
[11]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82.
[12] 辛斌.互文性:非稳定意义和稳定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5).
[13] 同上.
[14] Bakhtin, M.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M].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276.转引自辛斌.互文性:非稳定意义和稳定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5] 辛斌.互文性:非稳定意义和稳定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6] 苏州博物馆新馆. 贝聿铭与苏州博物馆新馆[DB/CD].南京: 江南音像出版社,ISRC CN-E32-07-0005-0/V.G.
[17] 信息源自笔者在苏博进行田野调查时对《画屏》展执行策展人许洁女士的采访。除文中论述的考量范畴以外,还有借调展品的具体难度。
[18] 赵墨.银烛秋光冷“画屏”[J].中国美术报, 2019(4).
[19] 信息来自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时对苏博展览设计部员工王振先生的采访
[20] 刘怀玉.《空间的生产》一书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此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空间化理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13JJD710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研究”(11BZX0005)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资助课《祛魅的现代政治世界——一种空间批判视角》的阶段性成果,引自:https://ptext.nju.edu.cn/c0/39/c13501a245817/page.htm
[21] 刘王铭玉.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巴赫金思想研究[J].外语学刊, 2011(11).
编辑:黄碧赫 孙小蕊
设计:魏敏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