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高远的《全球化视域下的双年展体系与在地性》(原载:王璜生主编、沈森执行主编《新美术馆学》研究文辑第1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作者首先回国双年展的发生和其全球展示体系,认为双年展并不是一种发明,而是早期全球化的历史产物,进而由文化政策、双年展制度及其公共性,认为超越后殖民话语,超越“异国情调”式的猎奇心态,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全球化视域下的双年展体系与在地性
文 | 高远
今天,双年展早已成为艺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各地每时每刻都有不同的双年举办,关于双年展的学术讨论也层出不穷。双年展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即使在反全球化语境下,学术界依然会以全球化的视域审视双年展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并讨论其在地性。关于双年展的学术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双年展举办地的文化语境与双年展整体架构的联系体现在何处?双年展的学术组织与艺术市场体系的关系是什么?双年展体系的全球化扩张是否带来双年展的多样化?
在全球化视域下,艺术的创作、展示、流通都在变化中,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全球双年展的历史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就算在“反全球化”浪潮中,双年展体系的扩张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因为这个体系并不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在符合在地性和文化语境的前提下进行调整,这一点不仅确保了双年展世界体系的多样化和跨文化性,避免了双年展的同质化,同时又使双年展体系不断更新,不断激发新的可能。
一、双年展的全球展示体系
当代艺术的跨地域、跨文化以及跨媒介的特性,在国际双年展的舞台上愈发凸显。就如1997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杰勒马诺·切兰特所言:“双年展和文献展这样的大型世界性展览必须以现在时的方式记录一个日益扩大的世界,以及不断变动着的连接历史与未来事件的记忆。”【1】如此宏大的立意似乎是艺术难以承载的,但是我们纵观世界各类国际双年展,可以发现很多双年展都是包罗万象的宏大主题,而在如今这个微小叙事和地方性话语早已取代了全局性的现代主义进步叙事的时代,这样包罗万象的主题是否能产生意义也是每一届双年展策展人所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在这种普世性主题的笼罩下,与艺术相关的具体问题的讨论是否可以生效?地区与在地性话语是否得到了积极的展示?具体作品在展览中的位置和作用是否得到了彰显?我们以威尼斯双年展为例(图1),纵观其历届的主题定位:“全世界的未来”(2015)、“百科宫殿”(2013)、“制造世界”(2009)、“艺术万岁”(2017)、“艺术的基本方位”(1993)、“跟着感觉思考,随着思想感受——世界艺术现在时(2007)”等等,不难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而关于这些主题的讨论也逐渐生成了当今双年展的知识结构。这些主题可以归纳成三个基本问题:今天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如何参与当今世界的建构?艺术的未来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从艺术的本体论到发生论,再到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全面地对人类当下与艺术相关的问题进行梳理,从某种意义上定义了什么是艺术的当代形态以及当代艺术的历史合法性。

图1:威尼斯“大运河”沿岸的历史建筑景观(作者拍摄)
从这些宏大又颇具深意的主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双年展并不是特定时代世界艺术作品的集中展示,而是基于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特定事件汇集成的文化、政治、经济现象中选取具有当下普世价值的主题,再将符合主题范畴的作品归纳梳理和呈现。如此看来,具有世界眼光和敏锐问题意识的策展人的角色就变得十分重要,他们往往具有世界级艺术博物馆或者当代美术馆长期的策划经验,对于全球性议题把握精准,并具有全世界艺术和学术资源的沟通和联络能力。
国际策展人的视野及对于艺术终极问题的把握成为国际双年展全球化扩张关键因素,而这种扩张的实质是文化资本/产业的扩张。展示全球范围内有代表性的新艺术、隔一年举办一次,这两条简洁的描述似乎已经成了双年展最基本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加上特定地区文化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政治的格局,才形成了全球双年展体系。这样一种体系关照的是全球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以及由艺术延伸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新涌现出来的问题的集合。在这个体系之下,全球各大双年展之间也在互相参照和影响,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文化资本的逻辑。这其中,威尼斯双年展无疑是最具参照性的。自1895年举办第一届以来,这个名副其实的“双年展之母”还在持续发挥自己的文化影响,继承了威尼斯自古以来的海上贸易城市的基因,将“文化”与“产业”密切结合,“艺术”与“经济”紧密靠拢,构成了威尼斯雄厚的文化资本,也是威尼斯双年展的根基。(图2)

图2: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城堡花园展区海报,2019年(作者拍摄)
随着1990年代当代艺术体系的全球化扩张,亚洲的“国际双年展”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与欧美双年展不同的是,亚洲国家的双年展大都创办时间不长,往往比较多地在国际层面展示本国艺术家的作品。亚洲国家纳入国际当代艺术体系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但是发展极为迅速。近年来双年展在亚洲的全面开花预示着亚洲国家有打破欧美当代艺术垄断局面的强烈愿望。“对亚洲大多数官方双年展的组织者——甚至对大多数策展人和艺术家来讲,双年展以把场地,作品,艺术家和策展人从‘国家’层面提升到‘国际’层面的方式运作。”【2】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也是亚洲争取更多双年展举办机会的合理诉求。双年展在亚洲比较有影响的如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光州双年展、台北双年展、亚洲艺术双年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沙迦双年展(Sharjah Biennial)、达卡双年展(达卡艺术峰会)等等;新近一些的有印度科钦双年展等;而中国的上海双年展也是至今仍持续举办的(国内一些“双年展”如“成都双年展”、“广州油画双年展”、“南京三年展”等由于种种原因停办或者改办)在亚洲比较有影响力的双年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双年展在中国经历了一种井喷式的发展。各个城市纷纷推出了双年展,从早一些的上海、北京、南京、成都、广州、台北,到新近的武汉、深圳、银川、大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等,中国的双年展阵势似乎有铺天盖地之势。但实际上,有很多展览只是借“双年展”之名,实则并没有或者缺乏符合全球双年展体系的作品和展示。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年展”招牌的举足轻重,以及清晰梳理“双年展”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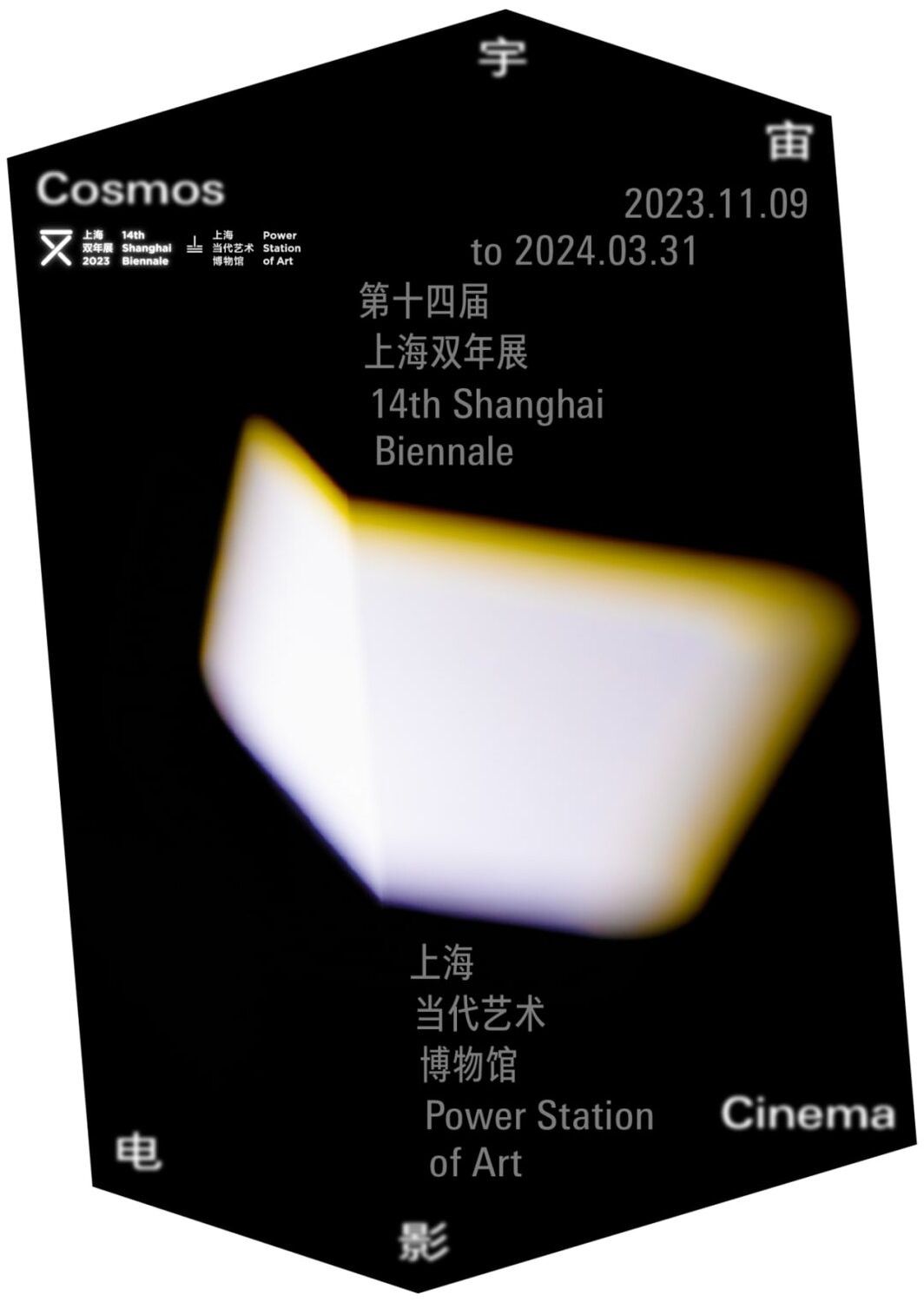
图3:第14届上海双年展主海报,2023年11月-2024年3月
可以说,双年展并不是一种发明,而是早期全球化的历史产物。换句话说,双年展体系始终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更新过程而产生的艺术机制。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早期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威尼斯双年展(1895)和美国匹兹堡卡耐基国际展(1896)应运而生。在当代艺术世界中,双年展是一种重要的组成,与艺术博物馆、画廊以及艺术博览会都属于整个艺术体系中的一种机制类型。与艺术博览会相似,它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性的,它只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存在,下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又会替换成其他的内容,这就决定了它的时效性:反映全球化浪潮的不同阶段。从最早的全球化时代开始,威尼斯双年展和惠特尼双年展都在特定时间节点上对时代做出了回应。双年展机制伴随着一种全球化的展示系统,艺术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局部现象,而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化体系之中。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双年展可以作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回响,在这次浪潮中夹杂着一种后冷战的全球化余波,在艺术层面就表现为政治异国情调的作品大量出现,这在我国“85美术新潮”及之后的艺术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的本世纪初期,独立策展人制度随着双年展制度的全球扩张而逐步确立。像哈罗德·泽曼(Harald Szeemann)、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恩威佐·奥奎(Okwui Enwezor)、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图4)、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等所谓“超级策展人”的出现也是全球双年展制度催生的产物。独立策展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制衡博物馆美术馆馆长的独断权力,他们在国际双年展的舞台上首先亮相,之后将他们的学术立场和艺术理想在艺术博物馆之外的城市空间、独立艺术机构中展示,而双年展被认为是“独立策展人”最理想的舞台。可以说,出色的独立策展人应该是双年展、博览会以及艺术博物馆和商业画廊之间的理想中介,他们沟通了这些资源并使艺术作品在特定体系内流通。双年展体系又生产出了更多的独立策展人,并通过他们,把双年展的展示模式和学术机制扩展到艺术世界的各个角落。

图4:策展人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 Photo by Casey Kelbaugh
二、文化政策、双年展制度及其公共性
作为城市观光经济和文化产业转化的最佳案例,威尼斯双年展又是一个绕不过的对象。这个自中世纪就称霸地中海的海上共和国,自中世纪以来依靠海上贸易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在历史上,其政府对于文化和艺术的投入极其惊人,其主岛上的建筑,每一座建筑都有其讲不完的历史;街角随便一处教堂,里面都可以见到贝里尼家族、维瓦里尼家族、提香、丁托列托、委罗内塞、提埃波罗、多纳泰罗、韦罗基奥等大师的名画和雕塑,以及桑索维诺、帕拉迪奥的建筑设计。这正是威尼斯的文化资本。如今它凭借深厚的文化遗存,创立了新的文化霸权——双年展,一个在当代艺术、电影、建筑、戏剧、音乐等领域拥有世界顶级的展事的文化巨无霸,使包括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士在内的全世界文化人士趋之若鹜。【3】威尼斯把握了整个文化资本的脉络,充分利用古代、近代、现代以及当代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以艺术带动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复兴,用重要的文化事件作为艺术事件发生的契机,最终在经济上获得丰厚的回报。
以欧美双年展对于文化产业增值的示范效应,伴随1990-2000年代的国际双年展热,双年展成为全球当代艺术展览的主流形式。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范围内的各类“双年展”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据统计,仅仅是在南美洲国家,就有19个“国际双年展”,世界各国也在纷纷探索具有全球化视角同时又具有在地性的双年展模式,作为本国文化战略中的重要组成。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也加入了国际双年展的行列。当时国内有一些展览虽然使用了“双年展”的称法,但其实质并不具有国际双年展的基本特征。饱受争议的“广州90年代首届双年展(油画)”在1992年的举办,是批评家借助新兴的资本力量以制度化规范艺术市场的首次尝试。(图5)

图5:1992年于广州双年展合影
(来源https://zhangxiaogang.artron.net/photo/?cyear=1992)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成为全球艺术的一部分(巫鸿,2005),但是还没有一个可以汇集世界范围内优秀艺术作品的制度化平台,而上海又是邓小平开放政策下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代表。地方政府与策展人经过了一系列的协调,在1996年“上海国际艺术双年展”(图6-7)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双年展,也是得到政府文化政策支持的第一个大型当代艺术活动。

图6:艺术家丁乙拍摄的96上海(美术)双年展新闻发布会,1996年

图7:艺术家周春芽拍摄的96上海(美术)双年展(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南京西路456号)展出时展馆的外立面,1996年
双年展模式的由来与欧洲现代意义上对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有着直接联系,对于城市替代性空间的利用,以及城市观光经济的发掘都是双年展举办地的初衷。从1894年的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始,双年展的历史已经走过了120多年,各国的代表性城市和地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双年展或n年展模式,同时也要使这种模式具有普世性和全球话题。从城市发展层面探索出适合本国的国际艺术双年展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始创于1996年的“欧洲宣言展”(Manifesta,图8)即采用了“游牧”的模式,将每两年一届的举办地游走在不同的欧洲城市,而这个城市也往往是远离文化和政治中心的相对边缘的城市,每届展览的主题和版块也尽量考虑到在地性。确实,国际双年展模式是否适用于某个地区,与所在城市的文化政策、艺术资源以及受众人群以及文化土壤都有直接联系;公众是否对双年展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如何都会是双年展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图8:2022年“欧洲宣言展”海报
当代艺术创作逐渐与公众脱节是近几十年来双年展领域甚至艺术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1990年代在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当代艺术的危机”正是这一矛盾的结果。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总是趋向于关照艺术体系之内的事情,而对艺术体系之外的因素考虑渐少。这种艺术不断地“自我参照”造成了现代艺术与社会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这也是所谓的当代艺术危机深处蕴藏的内涵:“社会整合与和谐不再或根本不再仰仗文化机制的合法性,‘为艺术而艺术’的确不是为公共空间而艺术,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真正成为一种无缘无故的、剥离了一切责任感与社会影响的东西。”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如今的双年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所谓的“文化圈”——上层社交界的小圈子中,刻意制造艰深晦涩的审美趣味,使其与公众隔离开来。这时候,实证主义和柏拉图拒斥艺术家的“理想国”似乎又起了作用,“一些蔑视当代艺术的人,蔑视的实际上是艺术本身。对于他们而言,商业、政治活动与财富生产远比艺术创造来得重要。”【4】认为当代艺术双年展脱离实际生活、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同,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源自于当代艺术活动与社会公众意义制造的脱节,当代艺术双年展逐渐被描述成一个精英文化圈的内部活动。这样看来,双年展的“公共性”问题正是双年展体系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从“公众”的概念到康德哲学的“公共性”,这种公众的、民主化的双年展即是一种“艺术乌托邦”,然而,在这个乌托邦里并没有看到公民平等地通过艺术交往的渠道,所谓的“趣味共同体”并未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世纪90年代的当代艺术双年展难以完成这样的使命。
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危机是一个前卫主义的历史问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在中国的一种在地性双年展现象。跟随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和调控,资本大量进入乡村和除城市之外的风景名胜区。在“打造文化旅游项目”的同时,一些实力雄厚的资本确实也支持了一些当代艺术活动。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近年来的艺术的乡村实践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一些策划人和地方政府也把当代艺术从都市带到了乡野,一方面迎合了国家政策层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也实践了艺术的公共性与在地性。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实验艺术活动中就有以艺术介入乡土的早期实践,到了2013年之后,一种结合了民国知识分子改造乡村理想的“艺术乡建”运动迎来了首个高峰。如今类似的方式已经成为中国艺术领域频繁出现的热搜词。但这类艺术活动离不开当今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资源的介入,国家层面的文化政策的支持导向更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近几年,艺术乡建运动也开始大量引进双年展的模式,“艺术乌镇”以及“安仁双年展”、“广安田野双年展”(图9)等远离核心城市的“去中心化”双年展的出现,调动当地居民或村民参与其中,在推进当代艺术公共性的前提下又兼顾了艺术的在地性。

图9:第二届田野双年展·红土地(2021)海报
双年展走进乡土,走向民间的方式不失为一种艺术公共性策略,在弥合当代艺术的公众性危机的同时,又加速了双年展体系的全球扩张。
三、超越后殖民的双年展及其在地性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大大改变了双年展的面貌。它不再只是西方前殖民国家在殖民地或其他国家推广自身艺术的展示活动。相反,“全球范围内的‘双年展化’(biennialization)促进了西方权力的消解,因此,‘双年展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反映,而是至少应作为非殖民化斗争的一部分,但斗争当然并没有终止于非殖民化时代(特别是在战后时代),许多前殖民地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象征性地争取解放的过程。”【5】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一些前殖民国家纷纷向其殖民地寻求“帮助”,比如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借助其早先的殖民地拉丁美洲和西北非诸国作为举办地,而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也成功推出了自己的艺术家并争取到更多的参展机会。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双年展上,非西方当代艺术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继圣保罗双年展出现之后,印度三年展,哈瓦那双年展,亚太双年展,光州双年展和约翰内斯堡双年展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双年展一方面扩张了双年展全球化的版图,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艺术曾经独断的话语权。印度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兰吉特·霍斯科泰(Ranjit Hoskote,图10)将在这些过渡性社会中涌现的双年展称为“抵抗的双年展”(biennials of resistance)【6】,这些双年展的出现即是为了制衡欧美双年展的独断话语,并且为非西方艺术争取更多的展示空间。

图10:印度策展人、文化理论家兰吉特·霍斯科泰(Ranjit Hoskote)
1951年开始举办的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开启了消解西方殖民话语的先河,但是其初期的模式却完全照搬了西方现代展览的模式,且参展的国家也只是西方国家;之后才逐渐引入了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越南、黎巴嫩和塞内加尔。通过参加双年展,这些新兴国家不仅自信地展示了‘自身的’文化,而且还加入了全球艺术史和西方的现代性体系。这类心理表征和行动惯例即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因此,早期的圣保罗双年展成为了展示“后殖民”艺术的窗口。
“后殖民”话语是非欧美国家任何一个国际双年展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的双年展发展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逐渐摆脱“后殖民”话语的过程。当今全球当代艺术格局在后殖民话语的基础上生成的各种跨文化变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对立格局。理论界对于二元对立话语的批判已经超越了如中心与外围、边缘与都市、民族国家与普世价值、全球与在地、权威与从属的区分。就如文化理论家霍米·巴巴论述的“第三空间”一样,只有在这样的中间地带,我们才有可能避开两极政治,以跨文化的协商方式,以文化混杂化抵消文化本质主义的霸权。从1990年代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双年展体系的全球扩张,双年展在中国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再到局部收缩,进入理性思考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双年展逐渐以一种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自身:逐渐摆脱文化猎奇与政治异国情调的视角,摆脱东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
超越后殖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各类艺术的“在地性”实践。把握“在地性”的目的在于凸显展览举办地的历史文化特质,使艺术事件在当地自然地生发,并融入当地的文化空间之中。在地性与全球化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但全球化并不是抹平差异,在地性也并不意味着排除影响。在地性是让更多的本土文化融入全球秩序,全球化是让更多的在地性串联成一个系统。就像经济领域的规律一样,艺术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展示,双年展也在这个体系中逐渐成熟并发挥影响。作为双年展主办城市所在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似乎不可避免。这种竞争体现在文化上,更体现在经济上。但是随着城市文化观光产业的繁荣,那种特殊的“在地性”也容易被他者化和同质化冲淡。理论家(Boris Groys)认为今天的世界城市出现趋同的倾向:“城市不再只是等待着游客们的来临──他们也开始加入全球的流动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复制自己,并向各个方向延伸出去。”【7】从历史角度把握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或许可以避免这种同质化倾向。就像威尼斯强大的海洋贸易文明基因所塑造的强大的“双年展文化”一样,其主要场馆就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打造了威尼斯海洋共和国的各大造船厂遗址。威尼斯、卡塞尔、伊斯坦布尔、柏林等历史名城举办的双年展,即充分利用城市自身的历史资源,加上当地文化政策上的全城各机构联动,使其难以被复制。如果想要扩大主办城市的资源优势,多城联动是个很好的模式。20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队就将希腊雅典设为分展场。当时深受债务危机波及的雅典也与德国卡塞尔市一道,共同作为主办城市呈现文献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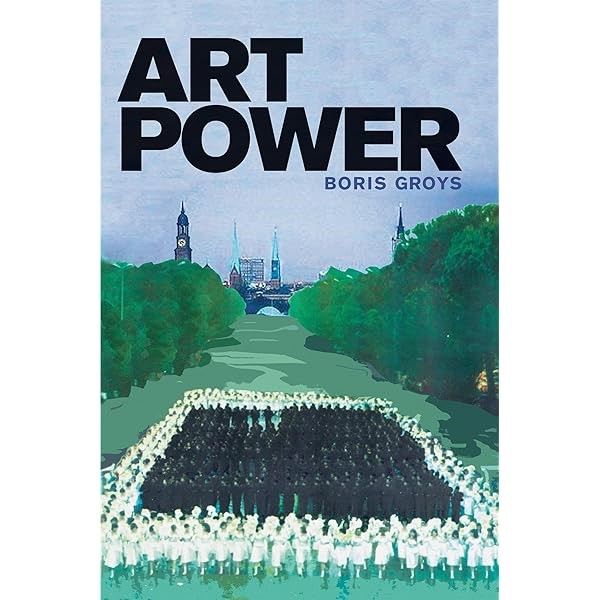
图11:鲍里斯·格罗伊斯《艺术力》(Art Power, The MIT Press, 2008)英文版封面
利用举办地点深厚的文脉,可以为双年展增添在地性的特质;把历史与当下融为一体,共同展示;设置多个双年展的分展场,呈现艺术的多重“在地性”与对周边的辐射性。艺术史学者、策展人姚嘉善(Pauline Yao)也谈及双年展之于城市和经济的重要性:“旨在吸引国际观众、创造文化资本并通过旅游业增加收入,双年展是体验经济(experience economy)不可否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目标商品并非某个单独的艺术品,而是城市和展览的整体体验。”【8】双年展的在地性体验与文化产业的充分结合,是全球各大双年展举办城市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威尼斯对于文化资本与历史资源的发掘,充分体现了作为商人共和国的基因。其市政府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了。威尼斯双年展不仅仅是艺术的双年展,更是文化资本的双年展,它展示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如何在当代焕发更大价值的故事。威尼斯把握了整个文化资本的脉络,借助自身在地深厚的艺术历史脉络与文化机制生成的逻辑。威尼斯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国际大展的参观和入场券,更应该有文化策略上的借鉴,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当代艺术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要靠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全球艺术家和观众,要借鉴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以跨文化的眼光看待特定的艺术问题,协调举办地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形成兼有全球性与在地性的双年展模式。
超越后殖民话语,超越“异国情调”式的猎奇心态,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国艺术家和机构参与国际知名的如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回想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艺术家和展览的大规模出现,那种非理性的趋之若鹜感觉近在眼前,中国的一些艺术家和机构也因凸显“异国情调”而被学术界所批评。在参与和自身发展国际双年展的历程中,中国艺术家和学术界也形成了今天看待国际双年展的理性前提: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去中心化的思维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双年展全球体系还在不断扩张,国际大型双年展仍然是重要的艺术事件发生场,也是真正的策展人展示能力的舞台,诸多重要的艺术家和艺术事件起初也是通过这些平台逐渐被世界所知晓。近年来,双年展全球化体系又借助中国乡土在地性实践,扩展至广大的村镇乡野、田间大地。中国当代艺术的去中心化实践借助双年展体系的效应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为全球双年展体系增添新的可能性。
注释:
【1】 杰勒马诺·切兰特:《1997年威尼斯双年展——未来、现在、过去》,易英译,《西方当代美术批评文选》,p.629
【2】 John Clark,Biennials as Structures for the Writing of Art Hist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The Biennial Reader,Hatje Cantz,2010,p.164.
【3】 参见高远:《中国的威尼斯?——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军团”》,《艺术当代》,2013年7期
【4】 伊夫·米肖,《当代艺术的危机——乌托邦的终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p. 74.
【5】 Oliver Marchart,The globalization of art and the‘Biennials of Resistance’: a history of the biennials from the periphery, World Art, Volume 4, 2014 - Issue 2.
【6】 Hoskote, Ranjit: “Biennials of resistance: Reflections on the seventh Gwangju Biennial”. In: Filipovic, Elena, Marieke van Hal, Solveig Ovstebo (eds.): The Biennial Reader. Ostefildern 2010, pp. 306-321.
【7】 Boris Grois, Art power, MIT Press, 2008, P. 105.
【8】 姚嘉善:《双年展制度之结构性批判,或双年展之未来》,载《南方以南:空间、地缘、历史与双年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9】 参见高远:《中国的威尼斯?——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军团”》,《艺术当代》2013年7期。
高远,研究者、策展人,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编辑 | 黄碧赫 孙小蕊
审核 | 沈森
审定 | 王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