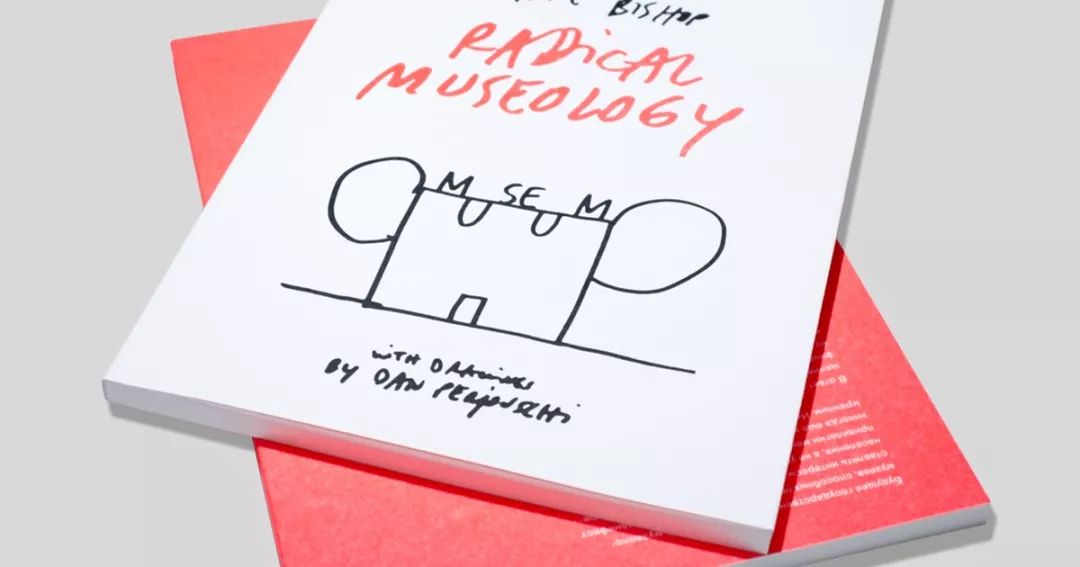
克莱尔·毕肖普《激进的博物馆学——或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当代性是什么?》
编者按:
我们近期推送所关注的问题:在艺术博物馆的公共空间所存在的一个重要悖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社区与美术馆的关系”,而展开对博物馆乌托邦式的构想和批判,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新美术馆学”的内容之一。由此,特别感谢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陈晓阳博士,以及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现任馆长曾玉兰女士,为本期的话题讨论供稿,他们的文章不约而同地对主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进行了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回应,各抒己见。
其中,陈晓阳馆长的《“他们”与“我们”:源美术馆的社会参与式实践》(2019年9月19日推送),从源美术馆在中国乡村的田野实践与实验项目,梳理了“社区”和“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的概念,揭示了乡村美术馆建设与艺术项目推广的困难与问题,也以重新发现“谁的风景”和“另一种设计”的观察角度,让艺术家、村民、美术馆在社区与美术馆的互动建构之中,重新阐释了前面所提及的美术馆的悖论问题,从而探索了“新美术馆学”在乡村实践的可能性。
曾玉兰馆长的《美术馆是“视觉游乐场”吗?》(2019年9月29日推送),则从美术馆实践者、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了对美术馆事业、美术馆学科发展和区域性与地方当代文化展览的思考,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该美术馆即将于2019年10月18日即将展开的展览《步履不停:1995-2019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城市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本期的《浅论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艺术博物馆的博弈》这篇文章,是我们的一位编者结合一些相关重要学术读物的读书心得与研究,试图对王璜生教授所提出的“新美术馆”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一点不成熟的回应,也希冀为艺术博物馆在当代“变形记”的某种新的可能性作出一点思考与探索。
浅论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
艺术博物馆的博弈
文/ 苏典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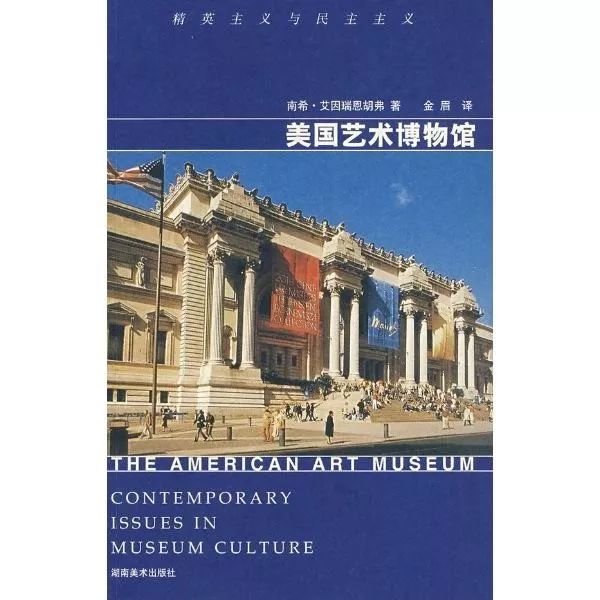
南希·艾因瑞恩胡弗《美国艺术博物馆——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
01
—
讨论背景:大众文化、大众与大众艺术
西方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与工业革命后一个城市中的下层社会形成的文化联系起来,起初带有一种不屑之意,英国当代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指出“大众(Masses)”早期具有“卑微”“地下”的轻蔑性,在20世纪后,变成了具有多重的含义,包含众多的数量、被采纳的模式(操纵的或流行的)、被认定的品位(粗俗的或普通的)和导致的关系(一种新的社会传播)。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受到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阿多诺等早期文化研究者的批判,坚持精英主义立场,认为大众文化是通俗的、消费的、一次性的、大批量生产的,不具有反抗或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知识分子才将早期被等批判的大众文化作为主体进行研究,颠覆了精英文化高于大众文化的传统观念,也企图消除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挖掘当代大众文化的民主主义的价值。
在17世纪的法国,lepublic(公众、大众)作为一个名词,不仅有国家或公共福利之意,也有lecteurs(读者),spaectaeurs(观众)和auditeurs(听众)三者之意,即作为艺术和文学的观众、读者和消费者[1],虽然此时的所指主要是指宫廷和城市贵族以及少部分的资产阶级上层,但从其词义本身,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大众”身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有精英的贵族气质,又具有公共领域活动参与者的普遍特性。那么如何理解大众艺术?美国当代理论家大卫·卡里尔就认为“大众艺术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艺术”,除去了观者与艺术品的历史距离,反映我们的生活。
02
—
博物馆的当代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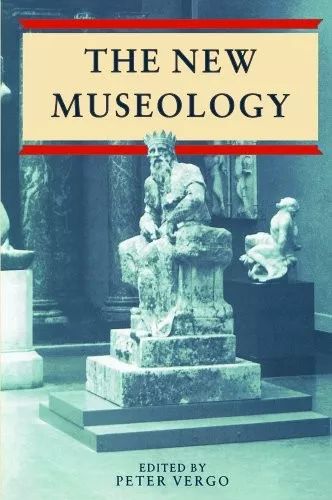
彼得·弗格《新博物馆学》
新博物馆学本身是8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思想碰撞中形成的,1989年彼得·弗格(Peter Vergo)的《新博物馆学》宣告新博物馆理论作为新兴领域正式进入学术领域。一方面新博物馆学本身阐述了对于博物馆的批评,特别是批判对博物馆的权威性的崇拜与敬畏,认为将博物馆作为圣地是一种精英主义范式,并不满足当代文化的需求了。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当代西方文化中对权力的膜拜是对抗后现代主义的相对性和文化商品化的一种策略,从而将博物馆视为非中立空间,且是个人所作的一些主观选择,以构建真实性否定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其理论自身也体现了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博弈。
就博物馆本身而言,艺术服务大众,或者说公共教育是许多艺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如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者一个重要的单项任务(如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但博物馆的内在结构亦是精英主义的机构,而展览的现当代艺术作品本身又具有无从接受性,如何使这类艺术作品民主化,成为了博物馆的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主要对抗表现之一。虽然说博物馆服务的受众数量是一个博物馆是否完成了为普通大众提供教育机会的民主使命的重要指标[2],但是各种当代艺术展览上观众量不断上升,观众却更多只是出于好奇和窥探的心理动机参观展览作品,并没有对于藏品有足够的了解,大众依然被边缘化于当代艺术展览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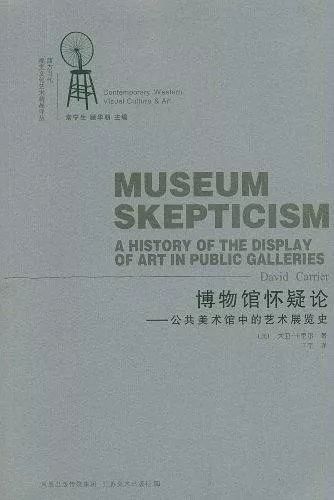
大卫•卡里尔《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
相比较而言,大卫•卡里尔所著的《博物馆怀疑论》,更提倡一种带来确定性的“触觉”。因为隔着玻璃展柜观看古老藏品无法确定视觉提供了可靠的知识,而这种“触觉”并不仅仅是指对手中之物的简单接触动作,而更多有一种“身旁之物”的触及的含义,这里的“身旁之物”在古代艺术品上似乎很难实现,因为我们几乎不太可能在博物馆和日常生活中触碰古代的艺术品。与此同时,卡里尔提到了“大众艺术就属于身旁之物”。大众艺术与精英艺术的关系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卡里尔把这个问题引向了与公共艺术博物的变形问题,认为公共艺术博物馆面对新挑战,就必须理解大众艺术和精英艺术的关联。
在卡里尔看来,完全民主的艺术是在流行文化里,而精英艺术在本质上是边缘的。但他并不像大多数艺术史学者那样具有排斥流行文化的倾向,相反,他试图做一种更为灵活的理解,这种灵活的理解的可能性是由安迪•沃霍尔及其追随者带来的。他指出,尽管(精英艺术者)竭力拉开与观众的距离,但是流行艺术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常常用流行艺术来讨论政治、文化变迁和价值观等。艺术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卡里尔的观点,自波普艺术诞生到后来的YBA,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当代艺术家们努力打破博物馆的墙壁,不愿意进入主流文化之中,最后却像现代主义艺术的各种流派一样逐渐成为艺术的主流,从游离的边缘进入了漩涡的中心,成为了大大小小的艺术博物馆的热门展品、藏品。
03
—
博物馆与当代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和来自大众文化中的材料持续不断地发生关系将会形成什么?卡里尔讨论了精英文化中的大众文化的作用,这是否也可以运用至讨论当代艺术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当代艺术也具有即精英文化里的大众文化的作用,或者说精英艺术里的大众艺术的作用呢,抑或是精英主义里的民主主义的作用呢?
按照这种假设,当代艺术自身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具有大众艺术的民主主义,当代艺术家力图与普通观众的生活拉近距离,渴望与观者的日常经验和认知发生某种关联,并大量运用现成品,是对当代文化生活与生存状的反映和思考。但这就出现了丹托所提出的问题,“当代文化的东西如此集中地与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作为我们文化认同载体的对象的意义,如果不了解其所指涉的知识与出处的话,就会丢失掉”,卡里尔注意到了,如此这般,“艺术通过借用实用品评论日常的意义就丧失了”,他将丹托的理论推及到所有的艺术上,认为这导致博物馆保存的只是古代艺术的实体,那么,按照丹托和卡里尔的逻辑,由于现成品所借用的原物丧失,让人们难以辨别艺术品与原物,是否也会导致博物馆保存的当代艺术品也只是实体的问题呢?这似乎是一个比较难解答的问题,因为当代艺术品需要大量的阐释,特别是观念艺术,而且现在各种艺术展览出现了同一件当代艺术作品以不同面貌出现,但由于核心观念和材料未变,依然是算同一件艺术作品的情况,很难判定博物馆只是保存了实体还是同样了保留了观念和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具有精英主义的特性,它需要大量的文本和观念阐释,正如巫鸿所言,是艺术家与理论家自觉地思考“现今”的状况与局限,以个性化的参照、语言及观点将“现今”这个约定俗成的时间或地点加以本质化。其作品的界定和批判依然是艺术界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当代艺术又更多是所谓的艺术圈的事,与通俗流行文化拉开了距离,也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甚至不为同在艺术圈的传统派,或者说保守主义者所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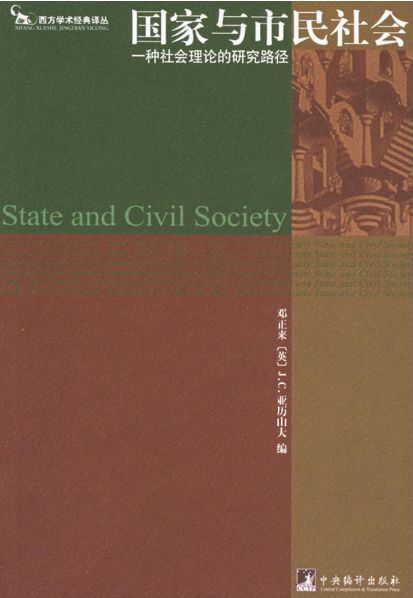
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8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批判之一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无视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实践。他曾提到博物馆使得业余爱好者对于艺术的评论建制化,讨论成为鉴赏艺术的媒介[3],公众成为了艺术评论的主体。哈贝马斯对于艺术评论和讨论的肯定,也许与民主一词在西方具有描述公开辩论的状态,以及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意义有关。
关于博物馆怀疑论问题的解决,受到哈贝马斯影响的大卫·卡里尔提到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观点,设想让精英艺术同大众艺术一样同样可以接近,即精英艺术除去了观者与艺术品的历史距离,成为与大众艺术一样流行的东西,让博物馆再次成为当下文化的一部分,博物馆的绘画雕塑就可以直接亲近。与常规上认为公共博物馆是供人们自由、民主地交流思想、感悟艺术品的公共空间的观点不同,卡里尔认为博物馆不是真正的公共领域,并没有让人们能够“展开讨论、辩论以及自由地交流看法”,也没有实现哈贝马斯所提倡的,“任何人有权对展览的艺术评判,审美价值是通过自由讨论确定的”。不过,他又提到,“博物馆如同大众艺术一样,使得一种广泛的对话成为可能”,因为融入了各种的对话声音,即兴的、随意的交谈享受不同的可能,这也是博物馆在当代变形的可能性的出现。

*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作者介绍
苏典娜,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研究领域为现当代艺术与批评、博物馆与公共美术教育研究。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博物馆通讯》2014年第2期,第19-22页,文章经作者改动并授权。)
[1](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变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郑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2](美)南希·艾因瑞恩胡弗,《美国艺术博物馆》,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3](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变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郑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编辑:苏典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