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这篇文章是美术博物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篇目之一。阿多诺通过讨论瓦莱里和普鲁斯特对博物馆完全对立的态度,揭示了美术博物馆从建立伊始就包含和艺术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使艺术永恒,一方面使艺术“死亡”。这个对立的关系的理解直接影响了后世学界对美术馆讨论的基本态度。
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1]
文/【德】阿多诺(T. W. Adorno)
译/郑弌
谨以此文纪念赫尔曼·冯·格拉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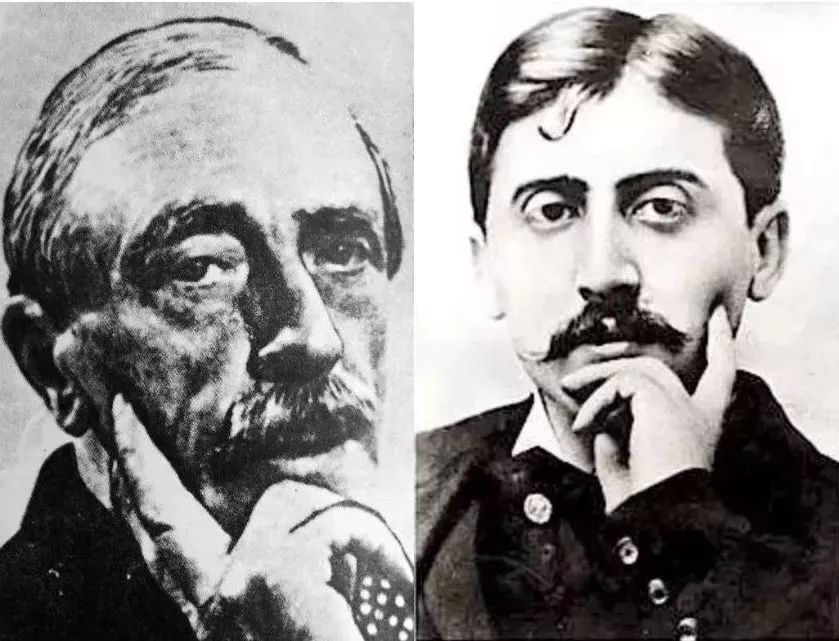
图1 (左)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
图2 (右)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
德语中的“博物馆”(museal,泛指博物馆类型的场所)一词所包含的言外之意,让人不快。它令观者与展陈之物间无法再保持着一种生动的联系,使后者趋向死亡。它们更侧重于保护展品的历史性,而罔顾当下的要求。博物馆(museums)与陵寝(mausoleum)间的关联之深,远甚于语音上的近似。博物馆就是艺术品的家族墓。它们佐证了文化的中立性。饱含艺术财富的它们,任由市场价值剥夺了纯粹观看的乐趣。然而,那乐趣无须附丽于博物馆而存在。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任何不曾拥有私人收藏(伟大的私人收藏也愈发罕见)的观者都只能在博物馆中熟悉绘画与雕塑。针对博物馆的不满如此强烈,以致让人们渴望将画作展示于其原初的情境中,又如放在一个类似巴洛克或洛可可式的古堡中。相比当初将艺术品带离其原始情境并放置在一起的做法,这样的结果甚至更让人忧虑。情绪性的宣泄对艺术的伤害也甚于驳杂的收藏本身。与此类似的是音乐与情境的关系。那些沉湎于复古情怀的大型音乐会曲目的安排,也已经愈发趋同于博物馆,就仿佛将伴着烛光演奏的莫扎特抽离为一出古装戏。试图将音乐从疏离的表演挽回到当下生活情境的努力,不仅徒劳无功,况且这努力,不过是些复归的怨曲。有些人曾善意地建议马勒,考虑到演出氛围,在音乐会时让大厅更暗些。作曲家恰如其分地应对道,倘若一场演出无法将周遭环境抛置一旁,那它就是毫无价值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说明,所谓情境问题的本质,即通常所谓“文化传统”。一旦传统不再由意义明确、意涵丰富的力量推动来有机地展现自身,反而借用“重要的是保持传统”这类教条召唤传统时,那么结果也只能是步向终结之途。一场实用美术的展览所自诩能守护的意义,只会引来嘲弄。任何视艺术能够藉由意愿来复制其原始形态的观点,都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陷阱。将往昔当代化,有损而无益。但倘若彻底放弃体验传统的可能性,则无疑是屈从于文化野蛮主义,背弃了文明的信念。尽管无序的世界乱象重重,而事实上各种补救也不过是拆东补西。
无论怎样,在普遍认为是负面情境的前提下,没有人会满意。一种明智的观点则希望博物馆人应当权衡各类观点。眼下就有两篇出色的文章在博物馆的问题上表述了自身立场。它们分别出自两位真正的法国前辈诗人。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但观点却并非针锋相对,事实上也并不违背对彼此的了解。在一本题献给普鲁斯特的文集中,瓦莱里强调他并不熟稔普鲁斯特的小说。瓦莱里评论博物馆的文章名为《博物馆的问题》(Le Problème des Musées),发表于文集《谈艺录》(Pièces sur l’art)。普鲁斯特相关的章节出现在《在少女花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filles en fleurs)第三卷。

图3 卢浮宫内
瓦莱里的观点显然针对卢浮宫庞杂而令人迷惑的馆藏。(图3)他写道,他并非博物馆的爱好者。馆藏的珍宝越是惊人,藏品的光彩便愈黯淡无光。瓦莱里用了“愉悦”(délices)这个词,恰是全然无法翻译的诸多词汇之一。“迷人”(Delicacies)像新闻语;“享悦”(joys)意义太沉重,过于瓦格纳了。“欢悦”(Delights)或许是最接近本意的,但所有这些词汇都无法表达那种对封建式愉悦的微妙追忆,后者让人联想起维利耶·德·伊斯勒·亚当(Villiers de l'Isle Adam)的《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德语中唯一与之相近的是《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中的“旖旎”(deliziös)。在卢浮宫,瓦莱里觉得君权式的权力语式从一开始就处处规制自身,包括拿走他的手杖和“禁止吸烟”的标牌。冰冷的迷雾压制在雕像间,他写道,僵直的躯体躁动不安,旁若无人而又凌乱地被排布着。站在供观者沉思的画作前,瓦莱里戏谑道,观者被神圣的敬畏占据了心灵;与作品的对话不过略大于教堂的静谧,而轻柔于真实的生活。观者只会忘了来此的初心:是追寻文化、愉悦,还是充实的需要,抑或是对惯习的遵从。倦怠和野蛮汇聚到一起。无论是一个享乐主义还是理性主义的文明都不会建构出这么一座如此自我割裂的场所。死去的图像已然安葬其间。
瓦莱里认为,相比于眼睛由绘画带入到视幻觉的遥远程度,耳朵距离音乐更遥远,最好闭上它;没有人能够要求它同时聆听十支管弦乐队演奏。此外,意识肯定也无法同时思考所有可能的选项。只有转动的眼睛被强制要求在某一刻去理解一幅肖像、一张海景、一间厨房和一场凯旋式;而最糟糕的是,截然相悖而驳杂的绘画类型。一幅画越美,它距离其他作品越远。它开始成为一个特例,独一无二的。有人曾说,这幅画杀死了周围的作品。如果它被忘记了,瓦莱里警告道,艺术的遗产将会被摧毁。就如同人的迷失,他的能力借助于外界的技术支持,因此无尽的财富也会让他枯竭。
瓦莱里的观点带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印记。他的确避免自身涉及有关政治经济的批评。这就导致了被赋予错误价值的审美考量不得不恰如其分地应对它被愈发惊人高估的事实。当他提及对无节制的估量以及由此导出的资本无用的结论,瓦莱里所使用的隐喻性表达对经济而言是有效的。无论艺术家的制作还是富人死去,任何一种情况都对博物馆有利。就像赌场,他们不会输,同时也是他们的诅咒。对于无望地迷失在美术馆的人们,洋溢在艺术中,却伶仃一身。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瓦莱里作为普通大众来看待这样一个情境,因而预设了在日趋肤浅的材料统辖下任何不祥的结果和过程。艺术成了教育与信息传播的载体;维纳斯蜕变成了文献。教育击败了艺术。尼采在他的《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中表达了极其类似的观点,“为了现世的目的而摆布、滥用历史”。博物馆所带来的震惊,使得瓦莱里将历史哲学角度引入到艺术品的灭亡中,并由此认为,我们已经让艺术病入膏肓。
即使走出博物馆,来到街上,瓦莱里依然无法让自身从博物馆惊人的混沌中解脱出来(也许有人会说,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一个对于无政府主义式商品制作的隐喻),他不得不寻找自己萎靡的根源。知识的魔鬼告诉他,绘画和雕塑就好比被遗弃的孩子。“他们的母亲已死,他们的母亲,就是建筑。当她在世时,她给了他们立足之地,还有意义所在。漫步的自由对他们是有限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地,明确界定的照明,还有材质。他们之间有着恰当的关联。当她在世时,他们明了各自所需。再会吧,这念头在轻语,我将永留于此。”在这样浪漫主义的姿态下,瓦莱里的评述终止了。在文末,他回避了激进文化保守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另一种结论:抛弃文化而非忠于它。
普鲁斯特对于博物馆的观点大多以其高超的技巧贯穿在《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temps perdu)的行文中。只有在那样的语境下,才能恰当阐释其含义。普鲁斯特的观点,代表了对前福楼拜小说技巧的回归,即不仅仅局限于对材料本身的表现上。他们通过潜在的联系密切地结合起来,并由此展开,正如叙事自身,在宏伟的美学自治体内展开他的内心对话。在说到前往海滨度假地巴尔贝克(Balbec)时,普鲁斯特评论韵脚的休止就好象生命中的旅程,“领着我们从一个名字到另一个名字”。韵脚的休止在火车站间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千奇百怪的地方……这么说吧,并不属于镇子的一部分,而它个性所包含的本质如此彰显,正如站牌上刻写着他们的名字那样”。就像普鲁斯记忆力求回顾的所有事物,似乎都被穷尽了作为对象潜藏的可能,车站成为了历史性的原型,同时作为出发和悲剧性的原型。在《加雷·圣拉扎尔》(Gare St.Lazare,图4)的玻璃罩下他写道,“在蜿蜒的城市上,它盘屈着;荒芜的天国里,尽是不详的戏码。曼坦尼亚或是维罗纳的天际如此现代,仿若巴黎。在这般穹窿下所发生的种种,或可怖,或可畏,就如火车的出发,抑或十字架的竖起。”

图4 克劳德·莫奈:《巴黎加雷·圣拉扎尔车站,火车进站时》,油画,81.9×101厘米,1877,现藏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福格美术馆
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与博物馆类似的转译。普鲁斯特狂热地喜爱着莫奈,正是他画就了这幅车站,如今属于国立影像美术馆(Jeu de Paume)的收藏。普鲁斯特将车站比拟于博物馆。二者都不是传统实践规制下的产物;而且有人或许会说,它们还都承载了某种死亡的象征。以火车站为例,它象征了远行这一古老的隐喻。在博物馆的例子中,它则隐喻了艺术品与“一个崭新却凋零的世界”(l'univers nouveau et périssable)的关联,一个艺术家们创造的新鲜而残破的天地。与瓦莱里类似,普鲁斯特一遍又一遍地回到艺术品的死亡上。他还曾提及,那些看似永恒的存在,实则包含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博物馆内那些预设的路径,正如普鲁斯特为火车站描绘的面相。“可我们这时代处处都沉迷于将事物置于其原本的情境下呈现于眼前,却因此压抑了其精神的本质。正是后者令它们出脱于情境。如今,人们把一幅画‘陈列于’家具、小工艺品、‘当代的’窗帘中。这琐碎而过分装饰性的陈列却是由一位完全不了解历史、也不曾在案头下过功夫的女士所作。然而,我们再也无法在用餐时感受到杰作所带来的愉悦,它只能也只会产生于一座博物馆中。在那的房间里,它们清醒地剥去了所有装饰性的细节,象征了艺术家能够退隐其中来创作作品的内在空间。”

图5 乔万尼·博尔迪尼:《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肖像》,1897。《追忆似水年华》中沙吕斯男爵的原型。
普鲁斯特和瓦莱里二者的主题之所以能够加以比较,是因为他们都认可一个前提,即艺术品应当是令人愉悦的。瓦莱里用了“愉悦”(délices)这个词,普鲁斯特用了“醉人的喜悦”(joie enivrante)。没有比这样的前提更典型了,它既体现了时代的差异,也反映了德法看待艺术的态度。早在写作《在少女花影下》时,“审美的享悦”(Kunstgenuss)一词在德语中听起来简直就像一首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的诗那般乏味。此外,瓦莱里和普鲁斯特将这种审美的享悦推崇到让人敬畏的母性地位,其概念本身却值得怀疑。对任何接近艺术品的人而言,它们就像自己的呼吸那样,并非仅仅是取悦于人的对象。就好比说一位游客评论建筑之美,又何曾了解所有的门道,周遭环绕着艺术品的他,就像是居住在中世纪小镇里的现代人,不由自主地做出肯定的评价。然而,只有当观者与艺术品间的距离得以建立,使欣赏成为可能,艺术品绵延的生机才能够显露。而这对任何家藏艺术且并非纯粹的游客而言,恐怕永远无从得见。但因为瓦莱里和普鲁斯特在创作同时也反躬自身,所以他们肯定能将各自作品所带来的愉悦传递出来。他们都认为某种刻骨的仇恨存在于作品中,也存在于竞争带来的愉悦中。面对这种仇恨,普鲁斯特像个德国人似的毫不退缩地加以肯定,正如沙吕斯(Charlus,图5)所假扮的那样。对他而言,作品间的竞争是对真相的检验。他写道,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指在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图6),像微生物般互相吞噬,挣扎求生。这种辩证法的态度,超越了固守于个体的立场,使普鲁斯特卷入与瓦莱里关于“艺术家”(artiste)的争论。它使普鲁斯特对博物馆固执的宽容得以实现,反之对瓦莱里而言,个人作品的存续则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图6 约翰·马丁:《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油画,136.3×212.3厘米,1852
存续的判断标准就在眼下,就在此时。对瓦莱里而言,当艺术把自己的位置让渡给生命的自觉性后,它就已经迷失于功能性的语境中了。对他而言,艺术品应用的可能性才是终极问题。他所设想的手艺人,使诗歌具有精确的轮廓,体现了对情境的注意力,而对艺术品的地位变得无比敏感,包括它的知识性背景。就如画家对景观的感觉加强了他对真实的感知那样,使作品有可能具备深度。他的艺术观是关于自觉性,却引向了最为莽撞的结论。他追随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直至否定的边缘。他使单纯的艺术品成为纯粹的对象,不可动摇的冥思,但他却如此细密审慎地检验它,最终发现如此纯粹的对象必然会枯萎、蜕变为商业化的装饰,丧失了自身的高贵。而这高贵恰恰是其“应然所在”(raison d'être),也是瓦莱里强调所在。单纯的作品受到物化和中性化的威胁。这是他在博物馆获得的压倒一切的认识。他发现,只有单纯的作品才能够保持严肃的观看,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在观看中逐出不纯的部分,而是指向一种社会化的语境。鉴于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所具备的不可腐蚀性,瓦莱里必须承认,艺术的地位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明日黄花;反理性主义和柏格森主义在他那儿也无处容身,惟有哀悼终将转化为遗迹的作品。
作为小说家的普鲁斯特,事实上接续了作为诗人的瓦莱里所止步的地方,即艺术品的后世。就普鲁斯特最关心的联系而言,艺术恰恰对立于专家和制作者眼中的自身。他首先是一个欣赏作品的消费者,一个业余者,倾向于感情外露;而对艺术家们,则高度敬畏那些出挑的作品,如临深渊。人们几乎可以认为,他的天才之中尤为突出的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甚至在生活中他也同样如此),而且如此彻底而精准,使其成就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成为内省与外在冥思的推动力,并由此强化,转化为回忆,以及无意识的回想。与专家相比,业余者在博物馆里感到无比惬意。瓦莱里在工作室里宛如家中,普鲁斯特则悠然于展览。在他关于艺术的观点中有些难以自洽之处,还有许多错误的判断,比如关于音乐的问题,将业余者的脉络推得太远(关于这点举个例子,他略显媚俗的朋友雷纳多·阿恩Reynaldo Hahn就影响了普鲁斯特小说,相关的文字句句都以确凿的口吻,无休止地煽情却毫不着调)。但他将这一弱点藏入自己的长处中,惟有卡夫卡可比拟。与瓦莱里相比较,无论他对个人作品的判断多么天真,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那些,他对艺术本身的观点却远非如此。如果对类似瓦莱里这样的艺术家说到天真这个话题,认为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对过程的自省与作品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则听起来近乎挑衅。但事实上,他对类似作品的范畴确信无疑这件事本身,就显出了自己的天真。他坚信无疑,他的想法、历史哲学的能力,也都强化了这一结果。当瓦莱里能够看见作品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它们经历变化的方式,范畴就成了标准。而普鲁斯特与那些创造作品的艺术家不同在于,他完全不受后者恋物癖的影响。对他而言,艺术品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远不止其特定的美学品质。它们是个体所观察到生命的一部分,并成为他意识中的一个元素。因此他察觉到它们中存在着一种与正统艺术品法则截然不同的层面。只有作品的历史演变能使这层面自由,它存在的前提是作品本意的消亡。普鲁斯特的天真是次级的天真。在意识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新的、更广阔的自觉性浮现。然而,瓦莱里将文化视作纯粹事物的保守观点承受了对历史性本质观照下某种文化体的敏锐批评,这种观照摧毁了一切事物的自足性。鉴于此,普鲁斯特最典型的认知模式,他对经验模式变化的高度敏感性,使他具有将历史风景化的认知能力,并获得相悖的结果。他崇拜博物馆,仿佛它们是上帝真正的杰作,后者在普鲁斯特的形而上学里从未完成,但永远在每一个个体经验和每一个原初的艺术直觉中不断更新。在他惊人的眼光里,他保留了部分童真,相对而言,瓦莱里则像成年人那样谈论艺术。假设瓦莱里能够理解些许历史的力量之于艺术作品和感知的作用,普鲁斯特便更明了,内在于艺术品自身的历史是怎样一个瓦解的过程。"Ce qu'on appelle la postéfité,c'est la postérité de l'oeuvre'"或许可以恰当地翻译为,“所谓后裔,即作品的来世”。就艺术品瓦解的能力而言,普鲁斯特认为它类似于自然之美。他将分解的面相视作它们第二次生命。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事物均非实体,但凡有实体者已经被记忆所改变;他的爱凝思着来世,已然结束,而非将始。对普鲁斯特而言,关于审美品质的美学问题是次要的。在一篇著名的短文里,他从听众记忆的角度赞美劣等音乐,比如一首陈旧的流行曲会比尽善尽美的贝多芬作品更精确持久地留在记忆中。记忆忧郁的凝视渗入文化的面纱。一旦它们不再孤立于客观意识的统领,而被引入主观意识的洪流中,文化层级间可悲的品质差异就会消失。瓦莱里的异端论调正植根于此。瓦莱里因博物馆混乱的一面而感到被冒犯,因为这歪曲了作品自我表达的实现;就普鲁斯特而言,这种混乱表现出了悲剧性特征。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博物馆中艺术品的死亡被带入现实中而已。他眼中博物馆的职能,就是将陈列与活态秩序分割开来,如此才能释放其真正的自发性——它的个性,还有“名字”,使伟大作品超越文化范畴的名字。普鲁斯特的表态,以冒险而繁复的形式,借歌德的《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中奥蒂莉(Ottilie)的旅行保留了下来,“任何种类中的完美者必将超越种类自身”,这离经叛道的想法给了艺术从相对主义角度反躬自身的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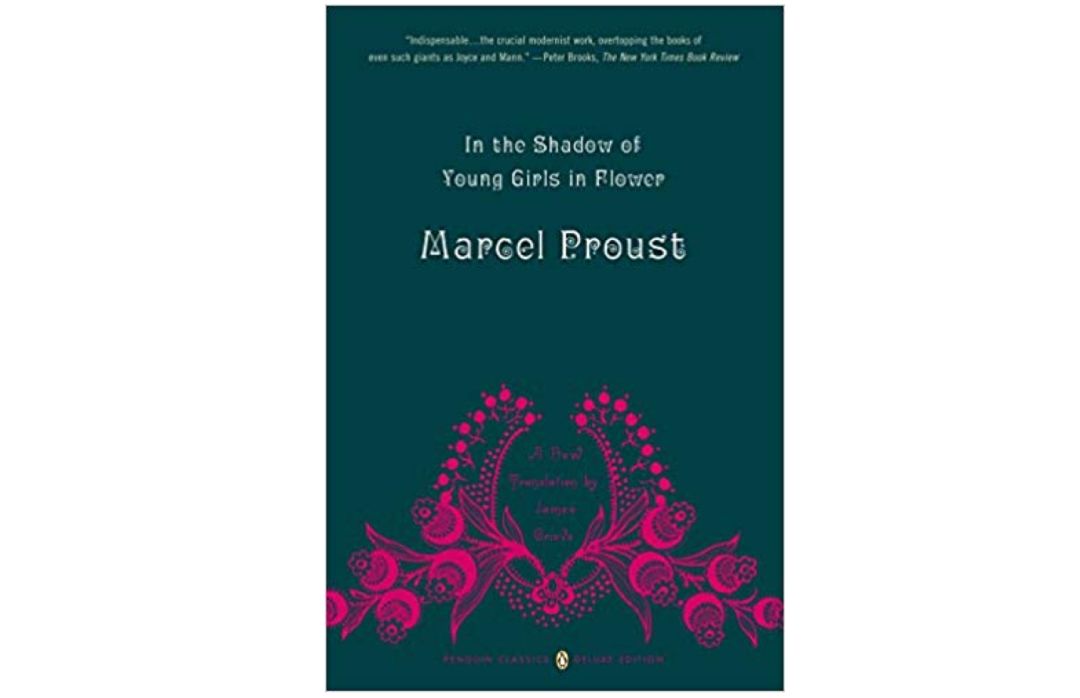
图7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
然而,任何不仅仅满足于知识史回溯的人肯定要发问:谁是正确的,博物馆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在瓦莱里看来,博物馆是野蛮之地。他的定罪,来自文化圣洁性(这点他与马拉美Mallarmé的观点相同)的观点,由此奠定了上述判断的基础。由于这种愤怒的宗教激起了如此多的反对,包括对其中过分简化社会性因素的异议,因此肯定它的关键时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只有因其自身而存在,而非为了取悦的目的,才能够满足人类的目的。很少有事物能如此去除人性,而意识的产物被证明只为薄荷般微漠的信念本身而存在,人类普遍的信念最终见证了理性的翻云覆雨。与主体的偶然性不同,瓦莱里能够在难以比拟的权威下展示作品客观的特征和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他借助主观体验作品的规律获得了他的看法。在这点上,他无疑高于普鲁斯特;他也无可动摇地有更多的抵触。相反,普鲁斯特将变动不居的经验置于首位,并拒绝容忍一切既定的陈规,这有着危险的一面。同样,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情境这样的观点则与柏格森相同。普鲁斯特的作品包括几篇谈论艺术的文章,其中以激烈的主观主义视角谈论低俗的姿态是如何将作品转变为投影实验的载体。相反,瓦莱里偶然也不无讽刺地抱怨,没有任何实验能够决定一首诗的品质。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Le temps retrouvé)第二卷(图7)中提到,艺术品就像某种光学工具供给读者,使他能够自我探究是否有其他可能。普鲁斯特支持博物馆的观点还体现在重要的不是在于陈列自身,而是观看的主体。这里面的主观性并非巧合,创作中的突发行为使作品不同于现实,这正是普鲁斯特认为将在博物馆的作品来世所保存下来的对象。就他看来,创作的时刻反映了作品同样的孤独,这也是瓦莱里所谓的烙印。普鲁斯特奔放的主观主义,使他并不执着于精神的客观性,也正是主观主义使他能够打破文化的固有性。
在二者悬而未决的笔墨官司中,无论普鲁斯特或是瓦莱里都不正确,也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供调和。他们的冲突以最具穿透力的方式使议题分歧更加尖锐,在互相驳斥中展开的讨论也使他们各执一词。迷恋于对象和主体性的沉迷使它们能够相互矫正。它们各自的立场彼此渗入。瓦莱里通过不懈的自我反省开始认识到作品中本质的存在,相反,普鲁斯特的主观主义希望艺术趋向理想,成为生命的救赎。因为反对以文化为目的或工具,他代表了否定性、批判性、自发性,这些都与纯粹存在不符。因此他公平地对待艺术品,只有当它们体现这种自发性的精华时,具备这类品质的才能被称作艺术。普鲁斯特坚持文化只能为客观的幸福而存在,然而瓦莱里坚持作品的客观需要迫使他放弃了对文化的希望。正是由于彼此矛盾的成分,因此这两位最渊博的人近期都写了关于艺术的文章,划清各自的界限,否则他们的知识实际上都难以成立。很显然,瓦莱里赞同他的老师马拉美,正如他在文中写道,“马奈的凯旋”,即存在与事物在此都仅供艺术来吞噬,世界的存在是为了创作一本漂亮的书并在一首纯粹的诗中实现自身。他还清楚地看见如何逃向“纯粹的诗”(poésie pure)所追求的地方。“没有什么如此明确地通向全然的野蛮”,他在另一篇文章开篇写道,“如此彻底地吸收了何谓纯粹的精神”。他自己的态度,将艺术抬升至偶像崇拜,事实上帮助了作品物化和瓦解的过程,而这正是瓦莱里所控诉艺术品在博物馆中所经受的过程。因为只有在博物馆,沉思,成为画作指定的终点,由此成就瓦莱里所期望的纯粹,而他却在认清自己梦想的恐惧中退缩了。普鲁斯特了解如何拯救这些。在某种意义上,当艺术成为观者主观意识洪流的元素时,艺术回家了。因此它们放弃异端的特权,并从印象派以英雄叙事和审美性为特征的侵害下解救出来。但出于同样的原因,普鲁斯特过高评价了艺术中自由行动的意义,就像业余者的意义那样。他时常以几乎精神学家的路数,认为作品应当完全成为个体内在生活的复制品,无论或好或坏,将它创作出来,享受它。他并没有完全看清事实,那就是在其概念里,总有某一个瞬间,作品需要面对其作者、观众,这是客观的,其自身内部结构和自我逻辑也会产生各种需求。正如艺术家的生活,只有从隔窗相望,才觉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自由”。作品既非灵魂的镜子或是隐含柏拉图式理念的映射。它并非纯粹的“存在”,而更近于某种介于主体与客体间的“力场”(force field)。瓦莱里所说的客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主体行动的自发性才能显现,普鲁斯特则将后者作为所有意义和幸福的惟一来源。

图8 意大利佛罗伦萨皮蒂宫内
抗议文化免于沦入野蛮的呼声被无视,并不仅仅因为瓦莱里抨击博物馆的论调有着堂吉诃德的一面,而是因为无望的抗议总是毫无必要。但瓦莱里的疑虑里有些过于天真,即博物馆应当独自负责绘画所经受的种种变化。即便它们仍然悬挂于贵族(相比瓦莱里,普鲁斯特始终与之关系更密切)城堡内的旧居里(图8),它们与展陈不过殊途同归罢了。艺术品生命中被侵蚀的部分依然是它自己的生命。如果瓦莱里迷人的寓言将绘画与雕塑比作失去自己的母亲的孩童,肯定有人记得在神话中,代表了人类从命运中解放的英雄,总会失去自己的母亲。只有当艺术品从出生的土地中连根拔起,走向通往自我毁灭的道路时,它们才能够完全实现“允诺的幸福”(promesse du bonheur)。普鲁斯特认识到这一点。如今将每一件艺术品归入馆藏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即便毕加索最晚近的雕塑也无从躲避。然而,这并非惟一要谴责的。它预示了艺术将要面临的情境:彻底地疏离于人,用诺瓦利斯(Novalis)的话说,回归生命。人们能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感受到这一点,在那里绘画与人的面相逐渐交融,毫不停歇;经验里回忆的线索与音乐的段落融合。在表述得最为明晰的一段文字里,《在斯万家那边》(Du côté de chez Swann)第一页描述入睡的文字这样写道,“我总觉得书里说的事儿,什么教堂呀,四重奏呀,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争强斗胜呀,全都同我直接有关”。[2]它弥合了瓦莱里所唱挽的无可调和的鸿沟。混乱的陈列消隐于孩童的赐福中,他们的身体能够感受到灵光的距离。
博物馆将不会关闭,也不值得去关闭它们。以自然历史收藏为指导的思想事实上已经将艺术品转化为象形文字的历史,并给予它们新的目录,而将旧目录束之高阁。无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哪种关于纯艺术的观念如此不合时宜地去抵消这一事实。瓦莱里因此不再展开他的观点,没人知道这是否胜过他的想法。但博物馆确定无疑地需要观者的参与,正如每一件艺术品所需。普鲁斯特曾经走过的那些身影,也成了过去的一部分。如今再也不可能让人逡巡于博物馆里,享受作品的愉悦。现实中,与艺术惟一可能被认可的关联,就是忍受持续威胁下的大灾难。以这种同样致命的严肃性对待艺术品的联系,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只有把自己的天真留在馆外的手杖和雨伞中,明确自己想要的,拣选三两幅画,目不转睛盯着它们,仿佛它们真的是偶像,才能避免瓦莱里邪恶的诊断一语成谶。有些博物馆在这方面颇有助益。除了光线和空气,他们采用的拣选原则正是瓦莱里所宣称,将人如在学校中引导,而后他便会迷失在馆中。在国立影像美术馆中,《加雷•圣拉扎尔》如今就挂在那儿。普鲁斯特的埃尔斯蒂尔(Elstir)和瓦莱里的德加彼此相邻,平静地各自身居其间。
[1]译者案:本文原名Valéry Proust Museum,选自特奥多尔·W·阿多诺论文集《棱镜》(Prisms),麻省理工出版社,1981;第173-186页。
[2]译者案:译文参见【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李恒基、徐继曾译《追忆似水年华(1):在斯万家那边》,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第3页。
作者介绍:郑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本文载于《大学与美术馆》(总第五期),文章经作者改动并授权发布。]
